和移工當鄰居 簡永達寫下勞動背後的血淚故事
【記者程庭軒、藍宇軒/桃園市大園區報導】《報導者》記者簡永達激動的說道:「這件事情就在我的身邊發生,但我們以前沒有在意過這些事。」簡永達住進第一廣場當起移工的鄰居是關注移工議題的開始。簡永達在第一廣場中看見移工與台灣有如平行世界般的氛圍,第一廣場裡面沒有中文字,他甚至以為自己才是外國人。簡永達和移工相處後提及:「如果只把移工當成勞動力,你只會看到他受傷、薪資問題,但如果你把他看成一個人,你會看見情感問題、醫療問題、休閒娛樂問題,這些需求讓他們從平面變成立體的人。」在他離開第一廣場後持續關注移工議題,寫下〈無國籍的移工小孩—「沒有名字」的孩子們〉、〈從台灣到越南,傷心的屍骨還鄉路〉、〈357等待職災補償的折磨——一名泰國移工之死〉、〈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臺灣搶攻危機〉等報導,這一切的經歷讓簡永達將報導匯集成一本書《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於2023年10月正式出版。

畢業於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簡永達,2015年中進入《報導者》,就被指派前往台中的第一廣場採訪移工議題,這對當時還是一位菜鳥記者的他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沒有任何人脈與資源協助,而且也對台灣移工的議題毫不了解。然而,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拒訪,他在2016年初毅然決定搬進第一廣場兩個月,親自與廣場裏的移工築起信任,深入田野進行觀察。
簡永達和移工兩個月的相處後匯集整理,寫下報導〈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他在裡面認識很多移工,他們有著不同的需求,像是:感情需求、娛樂需求,以及最重要的安全需求。針對移工子女的國籍問題,簡永達撰寫〈無國籍的移工小孩一「沒有名字」的孩子們〉,也曾陪同因工安事故喪生的移工家屬返鄉處理後事,看著移工遠離家人赴台工作卻遭不公對待,因此寫下〈從台灣到越南,傷心的屍骨還鄉路〉,此外簡永達陪著在台自殺移工的親人,在台灣爭取亡者遭剝奪的法律權益,寫下〈357天等待職災補償的折磨:一名泰國移工之死〉。
簡永達開始理解沒有好的工作政策環境就沒有辦法吸引移工來臺意願,他比較日本及臺灣的移工政策,深入越南「仲介一條街」將故事寫成〈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臺灣搶攻危機〉,最後簡永達將七年間的報導及所見所聞匯集成一本書《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沒有中文的第一廣場,有如臺灣的「平行世界」
2016年初,《報導者》記者簡永達首次踏進第一廣場(現更名為東協廣場),笑稱「當他走進第一廣場時,每個人的眼光都隨著他的步伐移動」,他第一次待在臺灣卻有著身為「外國人」的感覺,這裡的「平行世界」使他深感興趣。
「禁止臺灣人進入」寫在菲律賓的舞廳門口上,是簡永達在第一廣場中唯一看見的中文字,當他住進第一廣場時,發現這裡擁有酒吧、商店、舞廳、教會、美容美甲店、音樂展演空間甚至是水煙店等完整的生活機能,另他最震驚的是,在餐廳點餐時,菜單上面沒有任何中文字,簡永達笑著說:「第一次在台灣不能自己點餐。」當住了一段時間與移工朋友建立關係後,菲律賓朋友將外套蓋在身上「護送」簡永達進去舞廳,這是他第一次感到被認可和親近。
事實上,在2016年,台中市政府為了響應新南向政策而將「第一廣場」更名為「東協廣場」,一舉吸引更多其他地區的外籍移工造訪,根據勞動部統計,隔年人數成長將近一萬人,但簡永達嚴肅的說:「第一廣場與周遭環境是非常不一樣的,政府將此稱為東協廣場,稱他們為東南亞的想像非常單薄,是一個非常集合的名詞,但他們的國籍不同,文化、語言都不同,在第一廣場中每個國籍的界線非常清晰,越南、泰國、菲律賓、印尼人各自劃界在自己的文化中。」簡永達因此在《報導者》寫下〈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將第一廣場中的所見所聞,寫成一篇報導。
死亡及墮胎的領悟,移工不只是「勞動力」
簡永達在第一廣場認識一名印尼女移工,印女因緣際會下在臉書聯繫上同樣在臺工作的印尼移工,彼此產生情愫而交往,某日晚上印女打給簡永達哭著和他借一萬元,簡永達後來打聽到她懷孕了,男方要求她打掉孩子,但墮胎為伊斯蘭教的禁忌,女移工在身心靈摧殘下返回印尼,這件事讓簡永達非常深刻,他開始認知到移工不僅僅是勞動力,更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類,有感情問題、宗教信仰。
這經歷促使簡永達對於移工的生育問題產生好奇,而在《報導者》寫下〈無國籍的移工小孩—「沒有名字」的孩子們〉,在「屬人主義」的台灣中,要是父母親雙方皆為移工,生下的孩子將無法擁有與台灣小孩相同的受教權及健保權,且多數案例為印尼籍的移工產下的孩子,如故事相同受制於教義為主因,這些印尼寶寶不但不能取得台灣國籍,如果寶寶在台灣而並非在屬地主義的印尼出生,則寶寶將成為「滯留在台的無國籍寶寶。」
2017年的12月14日,桃園的一場大火造成了六名移工死亡,簡永達跟著其中一位死亡移工阮文薦的哥哥一起回到越南,一場大火後燒毀了原本洋溢在三代同堂20多人家庭的快樂,阮文薦離世後,他的哥哥阮文忠提到:家中異常的安靜,沒有交談、笑聲以及哭聲。」另一名死者黃庭預也是這場大火間帶走的移工之一,黃庭預的死訊迅速的傳回家鄉,幾個曾去過臺灣工作的男人聚在一塊,他們操著有口音的中文向簡永達抱怨:「去台灣工作很危險啊」、「我們住的地方沒有很好」、「我叔叔的兒子手指才被機器切斷」,這些話深入簡永達的內心,他開始看見移工在臺灣的處境,尤其是工作環境的法律權益,他將這段寫成報導〈從台灣到越南 ,傷心的屍骨還鄉路〉。
「危險之島」的悲劇 ,被忽視的移工職災補償困境
移工高危險的工作環境造成的損傷眾多,輕至在操作機器時造成手斷掉,嚴重至化學液體的潑散導致死亡,2019年7月16日,移工拜倫在位於桃園的「三永鐵工廠」被橋式起重機懸吊的鋼片意外墜落撞傷腹部,並在翌日送醫。但僱主卻並不承認這次職災。原因是事發當天拜倫並無大礙,而是第二天才送醫接受治療。而拜倫的胸腹也造成永久性的傷害,需要一直倚賴引流管進食。在漫長的養傷同時,他期望的職災補償卻遲遲等不到回應,在2020年7月7日,拜倫跳樓自殺了。
2020年的某天早上,拜倫的死亡引起簡永達的注意,他在臉書看到拜倫告別式的訊息。到達現場後,在那裏碰到了拜倫的兒子M,M透過旅遊簽證從泰國來到台灣照顧父親將近一年的時間,某天在M外出後得到父親自殺的噩耗,使得M在人生地不熟的臺灣不知所措,簡永達在告別式後一直陪同M處理父親的身後事,簡永達假裝不會中文,陪同M和臺灣的公務單位辦理相關文件,就是為了親身經歷體驗台灣人對移工的不友善,果不其然語言不通令他們阻礙重重,受盡事務所工作人員的白眼,也因為拜倫的個案打動着他,他開始研究移工的職災補償,撰寫報導〈357等待職災補償的折磨——一名泰國移工之死〉
台灣作為南亞移工的輸入大國,職業災害的傷亡率一直很高。根據勞動部統計,每兩小時就有一名移工出現職業災害,死亡率更是本國勞工的近三倍。但這些只是有記錄在案而且成功得到補償的數字,許多僱主因為害怕被勞檢,所以不會向政府通報。即使僱主願意通報,勞工局的職業災害認定過程也相當嚴格,要明確證明傷害與工作場所的確切因果關係,如果僱主在調查過程中不配合,移工們也無從追究。國家的補償機制上,需要由僱主及勞工共同承擔責任,例如拜倫的個案,僱主並不願承認責任,移工職業災害的索賠關卡重重,也令移工因為無了期的等待,以及瑣碎的立案程序從而不願意再申請職災補償。
保護移工的權益,與高齡化的東亞各國「搶人」
簡永達在2020年再次回到越南,深入越南紙橋郡「勞務街」,短短600公尺的街上聚集上百家人力仲介公司,負責招募、訓練越南的年輕人,輸出到日本、韓國、台灣等地做工,一位專門輸出越南工人到台灣的越南仲介經營台灣市場已16年,但過去半年,他已多次聘請翻譯陪同他赴日本拜訪客戶,仲介向簡永達說:「我看再過幾年,沒什麼越南人要到台灣工作了。」為此簡永達在《報導者》寫下〈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臺灣搶攻危機〉
根據越南政府統計,2019年全年約15萬名越南勞工出國工作,超過5成前往日本,約8萬人,台灣只有5萬4千人,差距持續拉大。
簡永達說:「台灣移工政策有沒有改變,攤開這三十年來看,移工政策不斷變化進步,但比較其他國家不斷競爭勞動力來源的情況下,臺灣的速度慢了些。」
東亞已開發地區的高齡化日漸提高,在亞洲地區「搶」東南亞地區移工已成為各國在經濟發展問題下最重要的事情,簡永達在《報導者》中的報導〈當日本變移工首選—越南一條街,預警臺灣搶工危機〉以日本及台灣為例,講述兩國不同的移工政策,日本的搶工政策,一波接著一波,從2019年開始修改五年簽證規則,使移工有機會利用檢定換取永住資格且綁定與日本國民相同的基本工資,日本官方與民間合作進一步在越南的河內城市周圍,興建大量的日語學校,2024年更進一步將技能實習制度取代為「育成就勞制度」,利用3年時間培育外國人達到一定技能水準,並促使擁有可長期工作居留資格的「特定技能」,且可以在相同業種自由更換工作。

簡永達將眼光放回臺灣,根據勞動部統計,114年1月底在臺移工總數為81萬人,但仍然沒有辦法申請永久居留權利。根據就業法規定,移工不得工作超過12年,家庭看護則可以延長至14年。而在2022年開始,推出「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工作超過六年,或者月薪達到$33,000的經常性薪資,並且符合技術門檻,僱主就可以為其申請成為中階技術人力,不受12年的居留期限制,甚至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但在轉換僱主的條件上便相對嚴格,例如原僱主死亡,工廠倒閉等等的條件,才能夠獲考慮審批轉換僱主。
簡永達坦言:「他跟我們所想像的自由轉換僱主仍然是一個不一樣的概念。」
簡永達將這些報導匯聚寫成一本書《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他在第一廣場中認識這些移工,開始知道移工的處境,寫下之後不同面向的報導,嘗試把故事告訴讀者,在2024年也獲得臺灣文學經典獎,評審提到:「他們是移工群體,也被還原成真實的個人。」
採訪側記:
第一次接觸台灣的移工議題跟他們面對的狀況。就像簡永達這本書的標題一樣,地下社會,像是有一埲無形的牆。明明他們卻活在我們的身邊,卻對他們充滿偏見與歧視,再進一步了解這個議題,以及親眼看到他們更多的經歷,開始了解為什麼簡永達要親身搬進去第一廣場,因為只有設身處地跟他們接觸,才能打破這道牆,看見他們在這裏工作,也在這裏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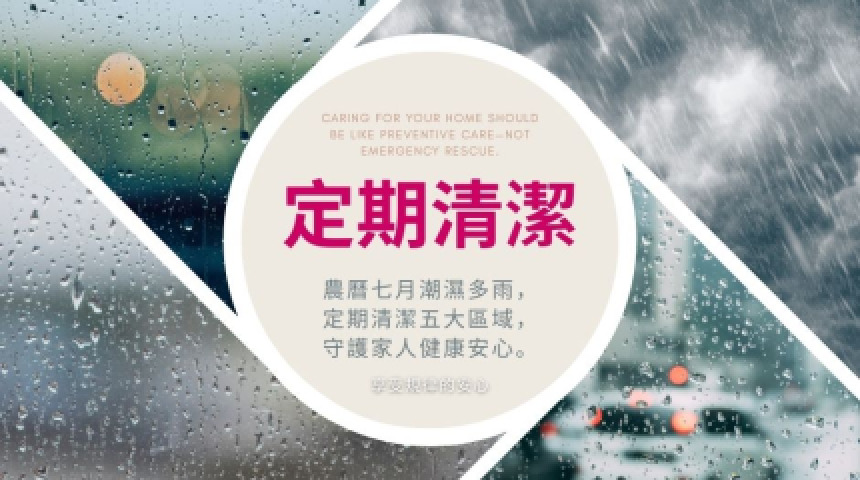

回應文章建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