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從來不會自己留下來 它必須被守 被記 被用 被活在生活裡
在那個會議室裡,她站得很穩,語氣不疾不徐,但每個字都像在替族人敲鐘——敲給那些坐在行政高位卻聽不見山林聲音的人。光線斜照在她的臉上,有一瞬間,龍應台筆下那些在歷史洪流裡倔強發聲的女人,好像重疊在她的影子上。她是伍麗華,一個穿梭在現代體制與古老文化之間的橋樑,一個知道「祖靈的聲音」不該只是神話裡的背景音的人。
她講的第一個故事,是火箭。不是NASA的,不是太空總署的,是落在旭海的那一具,落在排灣族傳統領域的那一具。試射過兩次,都以失敗告終。當時她沒有搬出什麼高科技解釋,也不是請更多專家來調整參數。她說:「我們是不是可以請 pulingaw 和土地打聲招呼呢?」
那一刻,很多人不理解她的意思。也許有人心裡偷笑,也許有人懷疑這是政治正確的表演,但她不在乎。她請來了張順枝 vuvu,一個族人,一個靈媒,在沙灘上對著天、對著海、對著風和土地敬告。火箭升空了。那一刻,她說,我們都知道,這不只是科學,更是與祖靈同在。
這句話,像一顆溫熱的石子,投進了文化部長辦公桌前那杯冷水裡。
她講的第二個故事,發生在遠方的愛丁堡。為了牡丹社事件150週年的祖靈遺骨返還,她和一群族人跋涉萬里而來。面對西裝筆挺的愛丁堡大學副校長與解剖學主任,她沒有用流利的英語發言稿,也沒有外交辭令的寒暄。她讓靈媒蘇寶珠站在前面,捧著一束祭品,像回部落一樣開始儀式。那不是演出,那是一場真正的告別式。
「他們感到的是幸運與榮耀,」她說,「而我們,只覺得終於帶家人回家。」
兩個故事,兩個文化現場,一個來自科技的最前線,一個來自殖民歷史的尾聲,都指向同一件事——靈媒文化,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不是迷信,而是活著的智慧。
她沒有停留在故事裡,語氣一轉,話鋒銳利:「我問文化部:政府還能做些什麼?」
她不是在撒嬌,也不是討拍。她是在清楚指出現實的裂縫。
她說,現在的制度下,靈媒文化難以取得「文化資產」身分,無法申請補助,無法傳承。那些願意回部落受訓的年輕人,那些還願意聽祖靈說話、學習儀式語言的年輕人,被行政程序擋在門外。有文化,卻無門申請;有意願,卻無力推進。
她停頓了一下,眼神直視文化部長李遠的眼睛,補上一句:「文化復振的路,如果政府不積極補強,就真的會斷裂。」
那不是語言的誇飾,而是歷史的寫實。
她提議:政府應帶頭,建立與原民會的合作機制,整合文化資產保存與傳統智慧保護的平台。她舉例,語推人員有制度支持,族語老師有聘僱保障,為什麼靈媒文化的守護者,卻沒有一條穩定的道路?
她說得更深遠:「他們傳承的不只是語言,更是祖靈的知識與信仰系統。」
那一瞬間,會議室像被打開了山林的窗,風從排灣高地吹進來,帶著檳榔葉的清香與老歌的韻律。那些被都市行政語言壓得喘不過氣的「文化」,開始發出聲音了。
她最後說起孩子們,她說起《哈利波特》。說起那些坐在都市書桌前的孩子,夢想著成為巫師,學會魔法。但她轉頭看著來自部落的孩子們,說:「對他們而言,這不只是魔法,而是真正存在的信仰與文化。」
「我們不只是復振一套文化,更是搶救一個民族對宇宙與生命的理解方式。」
文化部長靜靜聽著,沒有插話。他明白,這不是一場交辦的業務,也不是可以三個月內結案的計畫。
這是一場文化戰役,而不是補助方案的爭取。
這是一個族群,要對未來的歷史寫下「我們還在,我們還信,我們還唱」的聲明。
在伍麗華的語氣裡,有一種不捨。不是對過去的感傷,而是對未來的焦慮。她知道,文化從來不會自己留下來,它必須被守、被記、被用、被活在生活裡。
她站在立法院質詢台上,也像站在族人的山路上。她知道那條路不是直線,而是一條必須跪著走的信仰路。
她最後說了一句話,像刀劃開行政程序的包裝紙,露出裡面飄搖的火光:「原住民族的文化保存,不能等。再不做,就真的來不及了。」
那一刻,沒有誰再懷疑她的意圖,也沒有誰再以「傳統文化」當作博物館名詞來應對。她不是在懷舊,而是在救命——救一個民族的靈魂。
她說完這段話的時候,屋外天色漸晚。陽光斜落在會議廳的木地板上,那是文明的光,也是歷史的光。
如果你聽見她的話心裡有震動,那麼請記得,她不是在說故事,她在說:我們還有機會,只要你願意伸手。
——結束於文化的岔路口,未來的方向,由你來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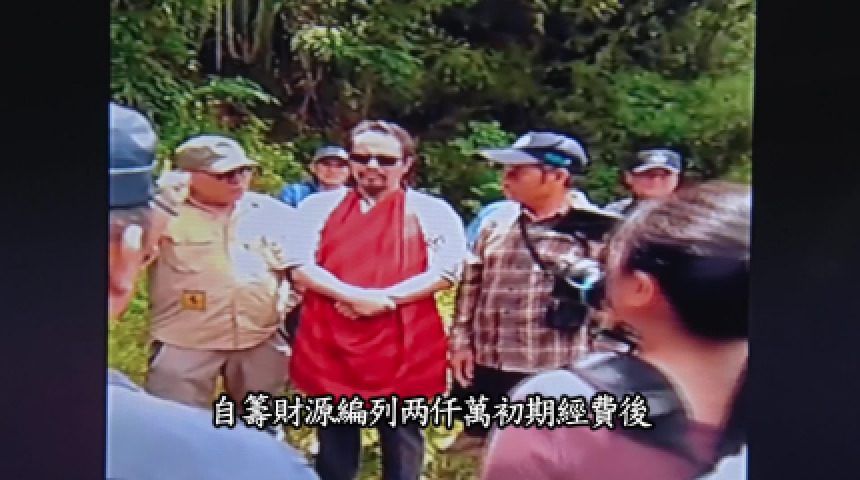


回應文章建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