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露手作雞毛撢子 拂去一甲子歲月塵埃
【記者張劭傑、范新玉/彰化縣埔鹽鄉報導】風吹過農村屋舍間的紅磚瓦牆,巷口屋簷下,幾束雞毛在陽光下曬得鬆軟蓬鬆。陳忠露拿起一根根雞毛,挑取根部沾上漿糊,熟練地貼在絲線上,另一手輕巧轉動木棍,將羽毛一層層黏合。揀選、旋轉、貼合,一把最質樸的清潔工具便逐漸成形,這是過去每個家庭都有的雞毛撢子。
在吸塵器尚未普及的年代,雞毛撢子是家戶清潔實用工具。它不僅可以用來打掃,更承載著戰後嬰兒潮的童年記憶與婚嫁象徵,蘊含著深厚的文化意義。

陳忠露家中早年以務農維生,但耕作的土地並非自有,而是向他人承租。由於田地狹小、農作收入有限,陳忠露的父親便向鄰居學習製作雞毛撢子。當時雞毛撢子是家家戶戶常見的生活用品,左鄰右舍都懂得這項技藝,因為製作流程不複雜,陳家也開始以販售雞毛撢子貼補家計。
1944年,陳忠露國小畢業後,白天協助家中製作雞毛撢子,晚上則到國中夜間部就讀。國中畢業後,他選擇不再升學,專心投入雞毛撢子的製作。陳忠露不斷強調,製作雞毛撢子絕不是可以賺大錢的職業,就算聘請別人來做,一天的工資早就超過販售的收益。但這是改善農家經濟困境、補貼家庭開銷的唯一出路,所以才選擇自己留在這裡製作,起初只是為了賺取生活開支,但漸漸地,陳忠露在顧客的正向回饋中感受到雞毛撢子的傳承意義,便以此為業,一路做到現在。
雞毛撢子不只是清潔工具,它也扮演社會文化中的多重角色。2024年,《金門日報》刊載一篇〈何處惹塵埃與雞毛撢〉的投書指出,「撢」與「膽」同音,因此女子出嫁時常會在嫁妝中附上一支撢子,象徵添了一份「膽子」。撢子作為打人的工具,也隱含「相夫教子」的意涵,呼應當時的婚姻價值觀,再加上「雞」與「家」臺語發音相似,所以有「起家」的祝福意味,是嫁妝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
因為雞毛撢子柄部堅韌,方便揮打,在鄉里言談與文學作品中屢見其身影。《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在我生命中的斷背山〉一文中,作者回憶因結交同性友人而被母親誤認性傾向的經歷,文中寫道:「她身上發生的,是被母親用皮帶或雞毛撢子一頓一頓的鞭打,以及迅雷不及掩耳的轉學。」揭示雞毛撢子在家庭空間中,除了清潔功能外,也是對孩子的懲罰工具,凸顯其在日常生活裡的能見度。
住在彰化縣埔心鄉、現年 76 歲的張郭秋瓜回憶,過去打罵教育盛行時,大人忙於工作,無暇照顧孩子,「不打不成器」的觀念深植父母心中。相比會打出血痕的藤條或塑膠水管,用雞毛撢握把處打孩子,已經算是最仁慈的懲罰,再加上當時彰化家中人手一隻雞毛撢子,因此只要犯些小錯,就常被雞毛撢修理。
農家遺落的羽毛,化為一甲子的撢塵人生
在彰化縣埔鹽鄉,一座人口不多、節奏緩慢的農村裡,81歲的陳忠露依然坐在木桌前,纏繞著一串又一串雞毛,就這麼度過一甲子歲月。從十幾歲開始,他就與這些輕盈堅韌的羽毛為伍,把人們眼中無用的雞毛,一根一根編織成拂去灰塵、撢去歲月的器物。
「早前不好賺錢,雞毛丟掉實在可惜,阿爸就把伊撿一撿。」國中畢業後,在父親的引領下,他開始學做雞毛撢子。當時家家戶戶都養雞、殺雞,羽毛堆積如山,卻因不如鵝毛輕盈、也不比鴨毛蓬鬆保暖,總被視為沒用的廢料,落在角落乏人問津。但在陳忠露父親眼中,這些看似無用的雞毛,因為沒有油脂而耐水、耐久,越放越有光澤,只要妥善利用,便能成為拂塵上選。陳忠露和父親一樣,把物盡其用的節儉觀念落實在手藝中,轉眼就是六十年。
對陳忠露來說,這份工作是一種能踏實活下來的方式。他豁達地說:「肯做就可以做,喜歡就可以做,錢雖然不多,夠用就好。」

毛根繞線、指尖功夫:撢子的手藝秩序
走進組裝的埕場,只有木桌、繩線、一大罐潔白的手工糊劑,以及一籃籃經過細心篩選的雞毛。這些簡單工具,正是他數十年如一日製作雞毛撢子的全部家當。雞毛撢子的製作流程並不複雜,卻極度仰賴耐心與雙手的熟練觸感。第一步,是蒐集品質上乘的雞毛。尤其公雞的羽毛,比母雞來得更長、更挺、更具光澤,是製作的首選。曬乾後的羽毛,還得經過篩選、比對,依照長短與色澤層層分類排列,追求視覺與實用間的細緻平衡。
接下來是製作的核心——「綁毛」。陳忠露將白線繞上木棍,單手熟練地拾起一根雞毛靠在木棍上,另一手則沾上糊劑,小心翼翼地旋轉、黏合。每一圈都貼合得恰到好處,等膠水乾了後,怎麼甩也甩不掉。接著是第二層、第三層……每一根羽毛的角度與位置都必須反覆確認,不能擁擠、不能歪斜,要齊整地向外綻放,展現出有序又柔軟的張力。
陳忠露謙虛地笑說:「做雞毛撢子是很簡單的事,任何人動手都做得來。」不過,要讓撢子不只外觀好看,還能經得起長時間使用、不掉毛、有效吸附灰塵,這背後講究的,是他數十年累積的經驗與判斷。

走進鹿港小鎮,一支撢子的跨城之旅
早年,陳忠露會將製作好的雞毛撢子帶到鹿港販售。那時鹿港商業活動興盛、店家密集,清潔需求大,是他穩定的銷售據點。佛像莊嚴、神明桌講究,那年代又尚未普及吸塵器,抹布容易留下刮痕,雞毛撢子便成為最合適、最溫柔的清潔工具。
「鹿港人重商業,要拜拜就要擦得乾淨。」彰化縣文化資產協會會長許惠雯說道。陳忠露所住的埔鹽,是典型農村,養雞多、毛源充足;而鹿港自清代以來商業發達,店鋪林立、佛具店密集,對清潔用具的需求旺盛。陳忠露年輕時會騎著腳踏車到商貿發達的中山路、佛具店賣雞毛撢子。陳忠露回憶,早期父親製作的雞毛撢子,一根售價僅有七、八角錢;隨著鹿港商貿興盛,價格逐漸提升至一根兩元三角,一天可賣出兩百多元,成為主要的生活收入來源。

-
↑陳忠露總是很有耐心的指導製作雞毛撢子的要領。攝影/張劭傑

-
↑傳統的雞毛撢子教學工坊,也吸引很多遊客慕名前來參與 讓這項逐漸沒落的產業能夠煥發第二春。攝影/張劭傑

-
↑除了雞毛撢子,陳忠露也開發毽子、逗貓棒等新產品開創新市場。攝影/張劭傑
工繁利薄,雞毛撢子日趨式微
雞毛撢子除了是清潔的實用工具,也承載小時挨被父母拿撢子打罵的「疼痛記憶」,有時候還會在電影和電視節目中看見它的身影,用途並不單一。然而,隨著現代家庭普遍改用多樣化的清潔器械,雞毛撢子的主力市場逐漸萎縮。陳忠露坦言,過年大掃除仍是銷量較好的時節,但在平日,購買撢子的人大幅減少。需求銳減,也使得年輕一輩難以投入學習,徒弟難留,傳承更難。
「年輕人在都市一個月可以賺三萬塊,這三五塊的工錢,沒有人要做了。」陳忠露比誰都清楚,這門技藝製作簡單但要花很長時間,加上純手工利潤低薄,不是輕鬆的職業。他理解年輕人選擇離開的理由,也認為自己能做的,就是把這一代的雞毛撢子做好。面對傳承問題,他保持開放態度,不執著於非傳不可,而是盡力走好當下每一步。
許惠雯也觀察到這一點。她曾在走讀活動中親眼見證陳忠露從挑毛、曬毛到纏繞的完整工序,深受感動。「每個步驟看起來簡單,其實環環相扣,非常有邏輯。如果沒有看到,你根本不知道一把雞毛撢子是怎麼做出來的。」許惠雯表示,未來希望能透過田野紀錄、講座分享等形式,讓更多人認識傳統工藝的價值。即便無法實質傳承技藝,若能成為文化記憶的延續窗口,也是一種保存的方式。
陳忠露依然持續製作雞毛撢子,也歡迎觀光客與校園團體走進他的二合院,一同體驗這門傳統手藝。現在除了雞毛撢子,他也會做一些扇子、毽子、逗貓棒,讓觀光客有更多選擇。以最受歡迎的毽子為例,將細小、短截的羽毛以線圈緊密綑綁,再固定於手縫的皮質底板上,不僅外型精緻可以當作桌上擺設,也是小朋友的實用玩具。陳忠露雖然沒有接班人,但他並沒有退休的打算,就如同當年不棄用一根羽毛的堅持,只要還有人參訪,或許他就會繼續做下去。

採訪側記
這次拜訪的埔鹽鄉是一個交通不便也缺乏各種資源的地方,陳師傅所在的住所更是一個人跡罕至的小巷中,比起人,更常見的反而是雞在散步,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個生活機能極度不便的地方,但陳師傅卻在那生活了60年之久,實在讓人佩服。以商業的角度來看,不去行銷長年埋首於製作這些雞毛罈子是愚笨的,但不知道為何,他執拗的堅持卻格外感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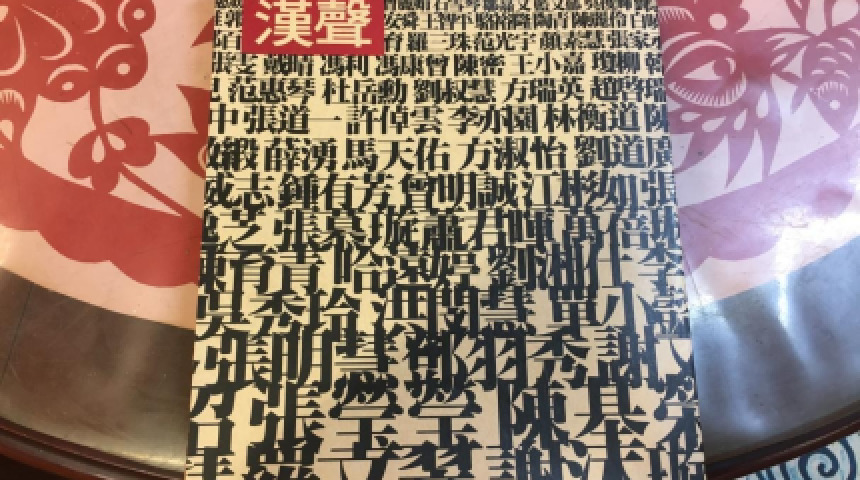
回應文章建議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