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時的最後美麗 修復遺體的魔法師

李安琪畢業於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碩士,從事遺體化妝師二十餘年,有遺體化妝修復「魔法師」之稱,也擔任過各類電影、戲劇的技術指導,經驗豐富,獲得許多家屬的高度信賴。
從事遺體化妝師的挑戰
原本擔任新娘秘書的李安琪,為了挑戰高薪而進入殯葬業。她表示起初對此類職業毫不認識,以為只是單純地處理遺體,應徵後去到工作現場,才知道生命禮儀的工作與程序複雜繁多,也因為服務對象變更為往生者,李安琪需要重新了解摸索相關知識,如適合往生者的化妝品選用等。
起初剛踏入殯葬業時,因為台灣社會對於此類職業仍帶有嚴重的刻板印象,像是黑道、找不到工作者等社會低階之人才會從事殯葬業,李安琪也同樣被身邊的人極度反對甚至貶低,認為她不需要將自己「降級」。較為傳統的家人更擔心她要跟鬼神「打交道」,例如時常遇到靈異事件等,所以當時幾乎不被大家看好,但她仍然堅持自己選擇的道路,一心專注在提升自我能力與適應新的工作環境。
遺體化妝、SPA與修復的流程
「人最後的面容會留在家屬的心裡,可能是陰影,也可能非常完美,這就要看化妝師的功力了。」李安琪表示,遺體化妝師的工作除了化妝外,也需要擁有SPA按摩及遺體修復的技術。
在化妝的步驟中,化妝師必須對遺體冰存後皮膚出水的情況,選擇適合的油性化妝品,確保妝容能附著於肌膚上。再來是徹底清潔面部,使用粉條進行遮瑕與打底。與一般化妝不同,化妝師需特別注意遺體的皮膚變化,如屍斑或暗沉,利用色彩學調色,使膚色看起來更自然。
而遺體SPA能讓家屬幫亡者洗手,與其道別。美容師分工合作,兩位負責身體清潔與按摩,一位專注臉部處理,並在最後替亡者化妝與整理髮型。
當逝者因意外或疾病導致面容嚴重損壞,化妝師需運用雕塑技術來重建五官的結構,這並非簡單的「修復」,而是對往生者外貌的精細重塑。修復師必須掌握人體結構與皮膚質感,並通過色彩學將蒼白的臉色調整為生動自然的血色,還原生命氣息。

生命的最後道別
在遺體化妝師李安琪的職業生涯中,有一段經歷讓她至今難以忘懷,她也將這段故事寫在她出版的書《打擾了,我是大體化妝師》中。那是一位年輕母親的告別儀式,她因患紅斑性狼瘡去世,留下了兩個年幼的孩子。這位母親離開了出軌的丈夫,為了養活孩子,甚至在身體狀況惡化後也堅強工作。讓李安琪感到特別心痛的,不僅是這位母親的早逝,還有她的孩子們在面對這個巨大悲痛時,展現的堅強和成熟。
儀式進行中,李安琪特別安排了兩個孩子與母親做最後的告別。當時,年幼的女兒在儀式上默默地忍住眼淚,當被問到是否願意幫媽媽洗手時,她點頭答應。女孩跪下來,輕輕為母親清潔雙手,並告訴媽媽:「妳可以好好休息了,我會照顧弟弟的。」讓李安琪和現場所有人都不禁落淚。
「其實容易共情的人很適合當遺體化妝師,這樣更能夠理解家屬並對這份工作感同身受。」這段經歷深深打動了李安琪,讓她感受到自己工作的真正意義。即便這份工作再辛苦,她也看到了其中的重要性。透過這樣的告別儀式,她不僅是為逝者服務,更是在幫助家屬,尤其是這樣年幼的孩子們,在生命的終點前,與最愛的人完成最後的告別。
遺體化妝的誤解與斷層
李安琪坦言,許多家屬對遺體美容師的態度仍充滿不尊重。她提到,有家屬會因美容師佩戴手套而感到不悅,甚至抱怨她們「髒」。然而,配戴手套是為了保護自身的衛生安全,這樣的誤解讓她感到心酸。此外,李安琪也遇過家屬粗魯地用腳踢設備的情況。這些行為讓她感到殯葬從業人員的專業性和人性化服務仍未被廣泛認可。
李安琪也表示殯葬業正面臨著人才斷層的挑戰。隨著年輕人對這個行業的興趣降低,許多從業者已經逐漸年邁,而新進人員卻寥寥無幾。她認為,年輕人往往誤解殯葬業是穩定高薪且輕鬆的工作,實際上這份工作不僅勞累,還需要高度的情感投入與技術專業性,高薪也必須靠自己的技術及接案量去爭取。
李安琪希望大眾能認識到殯葬從業人員的專業性與人性化,並給予她們更多的尊重與肯定。只有在這樣的互相理解下,殯葬行業才能夠繼續良性發展,並為更多家庭提供高質量的陪伴服務。
採訪側記:
採訪李安琪老師時,可以感受到遺體化妝師這份工作的重要性與辛勞,以及未來面對的挑戰。老師非常專業並分享許多經驗與故事,讓我們聽了十分感動,對於人的生死有更深度的理解,是個內心產生很多感觸的採訪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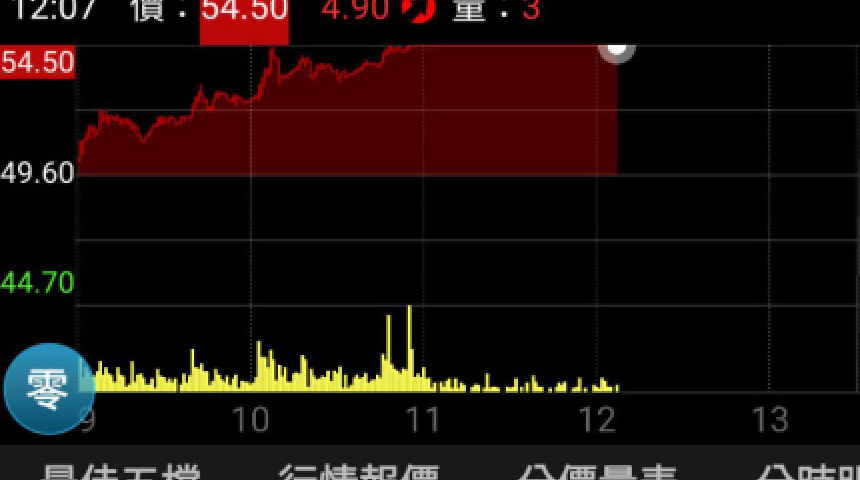

回應文章建議規則: